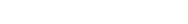作为上古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天子”一词的确切含义及其思想意蕴尚未获得一致看法。“天子”区分于纯粹治权意义上的“王”,具有非常深厚的政教意义。从文献出发,“天子”的内涵并非字面上的“上天之子”,因为在周人看来,“天生蒸民”(《诗经·大雅·荡》),下民皆上天之子。《尚书·召诰》有“元子”之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有王虽小,元子哉”。裘锡圭据此认为周人“天子”一词乃“天之元子”的省称,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基点。

“天子”旧说的检讨
但是,裘先生进一步以为“元子”的意思与礼学中“嫡庶”的观念有关,则不无可疑。因为就周人之天命转换理论构造而言,上帝拣选“天子”乃从另一层面展开。《诗经·大雅·皇矣》为周人史诗,描述了上帝“改厥元子”授命于周的全过程,其开篇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通观这一过程,天选之起点为“求民之莫”,“莫”,《毛传》:“定也。”彼时大邦殷之治已经引起下民的普遍乱局,上帝乃寻求可以“安民”者,以此眷顾周人。《皇矣》诗后文云“乃立厥配,受命既固”。“配”,《毛传》:“妃也。”《郑笺》:“天既顾文王,又为之生贤妃”,误。此“配”者,即“君”也,也即下文“作邦作对”之“对”也。“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毛传》:“对,配也。”《郑笺》:“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也。进一步说,准确而言,此处“王此大邦”者乃文王(而非王季)。诗中云“自大伯王季”者,乃追王之辞。《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要言之,《诗序》对此诗主旨的说法是非常准确的:“《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可见,上帝拣选“天子”整个过程的逻辑显然无关于嫡庶。换言之,天之“元子”的意义,无关于作为人道规定之礼学。治权之转换只关联于治理状况本身,所谓“求民之莫”。“元子”的意义需要重新考虑。
从“元子”与“一人”的互训谈“元子”的含义
与“元子”的称呼相关,文献另有“予(余)一人”的概念。对于“予一人”,礼家以为“天子自称”。《礼记·玉藻》:“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郑注:“余、予,古今字。”宫长卫认为“予一人”“余一人”或“我一人”都应视为同位复指,而实体是“一人”,“一人”才是天子专称。《诗经·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毛传》曰:“一人,天子也。”是也。
但天子何以自称“一人”,汉代以来异见纷呈。总体而言,传统说法多认为这是天子的自谦之辞,如《白虎通义·号》篇说:“王者自谓‘一人’者,谦也,欲言己才能当一人耳。”现代学者则注重其政治垄断的含义,胡厚宣认为它“充分代表了专制暴君的独裁口吻”。刘泽华亦有类似观点:“上帝与王同为帝,王具有人神结合的性质,因此,王同一切人对立起来,成为人上人,故自称‘余一人’。”
古今学人对“予一人”的解读显然分处两个极端。我们认为,“予一人”的称呼是殷周之王在天人关系的视野中对自己所处位秩的表述。它的内涵既不可能是说自己与万民相同,更不可能表述与万民的对立。
周人意识中“元子”与“一人”皆指代“天子”,显示二者之内在关联。以康王为例,《尚书·顾命》篇前半部分成王称呼其为“元子钊”,后半部分则自称曰“予一人钊”。我们认为,除去“自称”这一适用语境层面上的区分,二词表述内涵应一致。前文已及,周人意识中下民都是上天所生,即皆上天之“子”,故此,“元子”之“子”者,即“民”或“人”也,上古语汇中“民”的基本含义就是“人”。进一步,“元子”之“元”,即“一”也。所以,“元子”与“一人”二辞实可以互训。结合这一互训,我们认为“元子”及“一人”的含义是明确的,即“首子”,或说“第一民”。
此处,“首”字表述的等次内涵,既非血缘意义上,亦非礼学嫡庶长幼意义上。事实上,其含义毋宁说乃是抽象的,即上帝所降生下民中最符合其“造作本意之人”。所谓“造作本意”,以周人的观念表述,即作为物类之一种的人之“德”。或疑此处将“首子”中“人”的含义理解为“物类”意义上的“人”,外延过宽。然夷考许慎引春秋左氏古说有云:“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是“天子”一称针对的“人”乃兼括“夷狄”而言,是为“元子”乃是从“人”这一“物类”而言之证。这一点亦与周人天下意识中“民”观念的超部族性一致。
无论如何,最符合上天“造作本意”,乃上帝从万民中拣选“元子”之核心要素者。只有在这一意义上,《尚书·召诰》所谓“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中的“改厥元子”,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也就是说,彼时的“元子”人选已经不符合其“第一民”的抽象含义,需要改选更为符合的另一人。
“元子”的说法源于“元后”
事实上,从“元子”之“元”出发,在《尚书》学系统中,“天子”观念还可以找到更为悠远的本源。
今本《尚书·泰誓》篇载武王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聦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大禹谟》篇载上帝言:“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 材料虽皆属所谓伪古文《尚书》,但“元后”的概念是可靠的。《国语》载内史过曰:“《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如是则长众使民,不可不慎也。”可见,古《夏书》已有“元后”之称,而且明确将“元后”的观念与“余(予)一人”相关联。如果我们在文献判断上更为大胆一些,认同今本《泰誓》篇“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保留了古《泰誓》文本原貌,再联系《尚书·洪范》篇有“天子作民父母”的记载,那么“天子”一词源自“元后”的脉络就更直接了。
“元后”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晰的,指居于“群后(分散的部落酋长)”之上的首领。“天子”的基本含义也是这样,《礼记·曲礼》所谓“君天下曰天子”。《周礼·典命》职司有曰:“凡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誓犹命也。”对此,孙诒让《周礼正义》释曰:“凡经例皆称‘王’,此云誓于‘天子’者,对诸侯之称,《曲礼》云‘君天下曰天子’是也。”孙氏并曰:“通校全经六篇,称‘天子’者,惟此及司弓矢、校人、玉人、弓人五职,皆以对诸侯、大夫、士为文。盖与《曲礼》《春秋》义略同,非接上事天之号。”孙说极是。盖“王”乃有治权者的通称;而“天子”一号则重于表述王者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位秩,即超出诸侯大夫士之上者。这一点可谓与“元后”的观念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说《白虎通义·号》篇以来对“天子”一号来源的“接上称‘天子’者”的理解是错误的。
“元后”与“元子”二号皆是对王者基于自身德性而来的居于政治共同体首要位置的表述。不同之处仅在于,“元后”一称的参照系是“群后”,而“元子”的参照系乃“兆民”。
“元后”“一人”“元子”称号的政教内涵
据此再返观《皇矣》诗所展示的周人之天人观。“元后”“元子”居于“元首”位置,其始其终皆有赖于上帝的审度与拣选,其中渗透的政教逻辑在于,上天设置“元子”其位其人,端在于代其养民、安民,舍此职分也就无所谓“天子”,这一点为《诗》《书》通义。可见,上天拣选“天子”属于一种政治的托付关系。由此,亿兆民人生活之康宁与否,责任全集中于天子一人。文献中天子以“予一人”口吻的自言自语,反复述说的就是这一层沉重的责任,如“(盘庚曰)邦之臧,惟女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在这一托付关系之下,才有了天子一人上接于天的必要。也就是说,无此“代天”一层,也就无所谓“事天”。故而,周人之天子“事天”,不是《白虎通义》意义上的“事天”。《白虎通义》中的汉代观点认为,“接上”事天乃“天子”一号的本源,进而“天子”自然高于众民,这一逻辑事实上是一种神学政治的垄断。在周人看来,天子乃是由于“作民父母”而位居“一人”,“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才需要“事天”。故此,我们说周人的天子“事天”,虽然形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独占性”,但这一“独占”不能被认为是“垄断”,因为除了代天养民之外,天子并没有其他私密性的原因“接天”。
在《尚书》记录的上古三代正统政教意识中,从“元后”到“一人”再到“元子”,其基本意思是一贯的:君主德居万民之上,并因其承担的养民之命而沟通上天。周人于“元子”一词加上“天”的限定词并省称曰“天子”,是将其中隐含的天人关系明确化。相较于“元后”,“一人”与“元子”的视野是“民”,背后反映的是夏以来部落酋长性质的“后”之持续衰弱与商周以来“民”的地位日益凸显的事实。周人从“天生烝民”的神学政治出发彻底抬高“民”的地位,自此,“民”之一义成为华夏族政治意识的重心。从这一思想脉络出发,周人将政治共同体中的元首改称为“元子”“第一民”,就是很自然的了。
(本文获东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2232019H—02)资助)
( 作者:成富磊,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