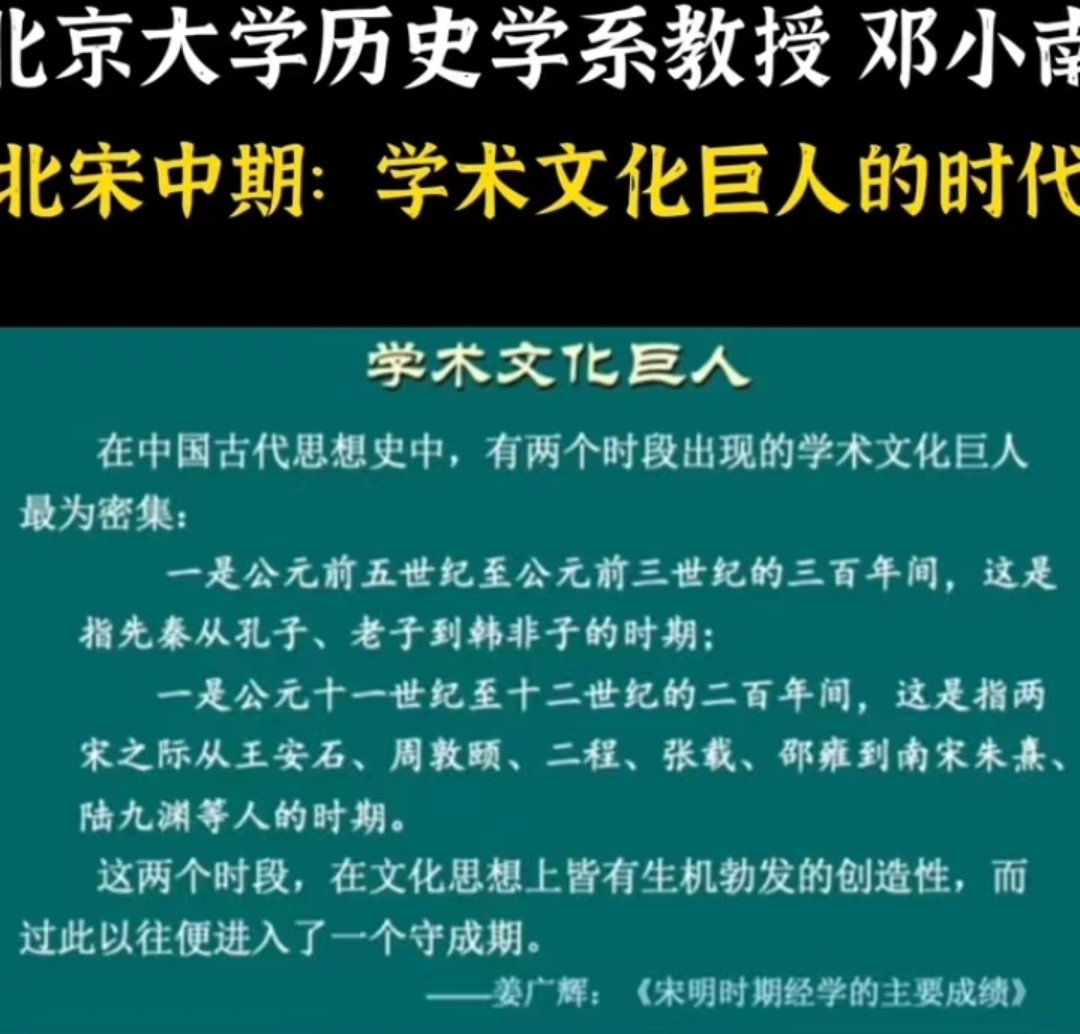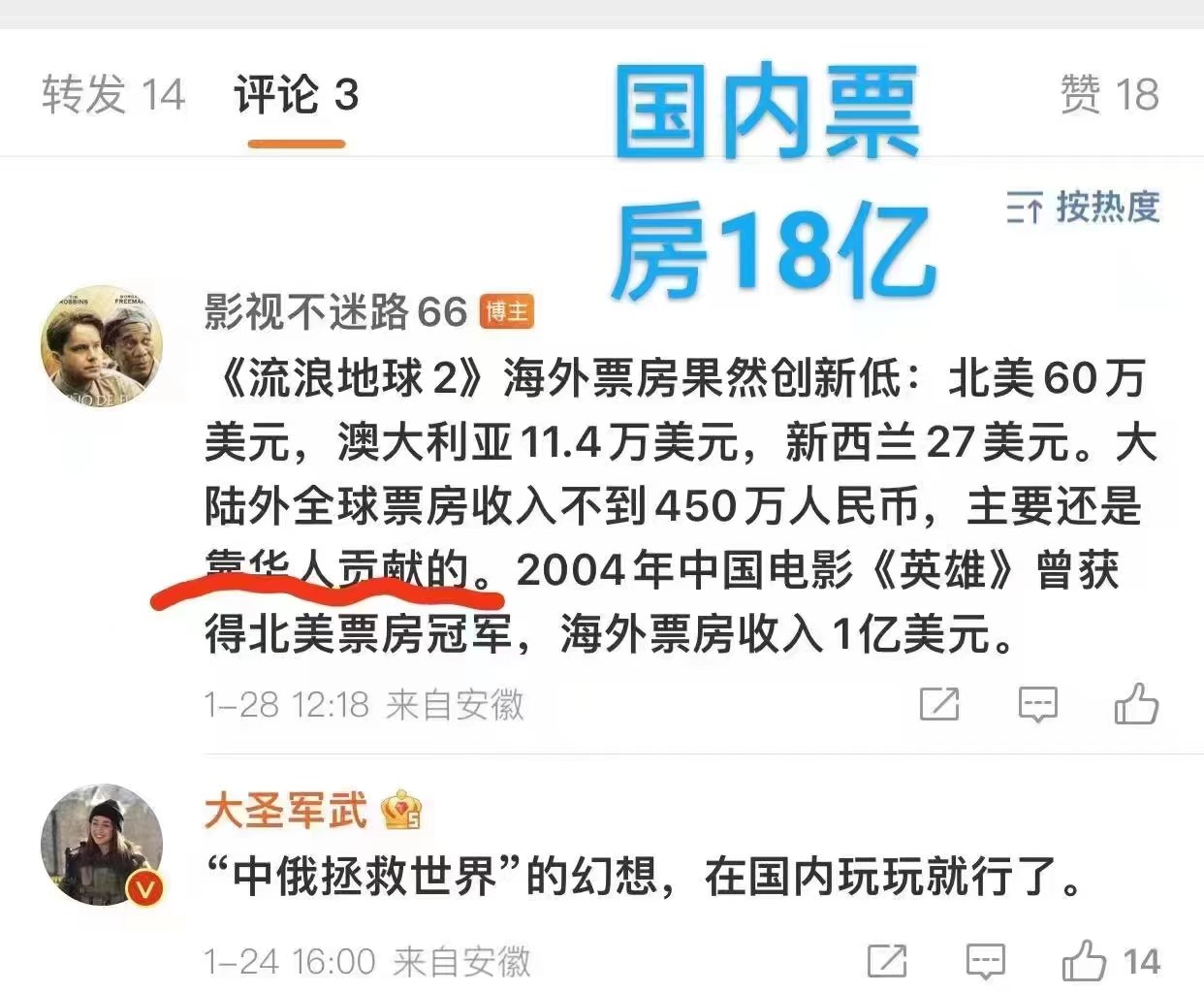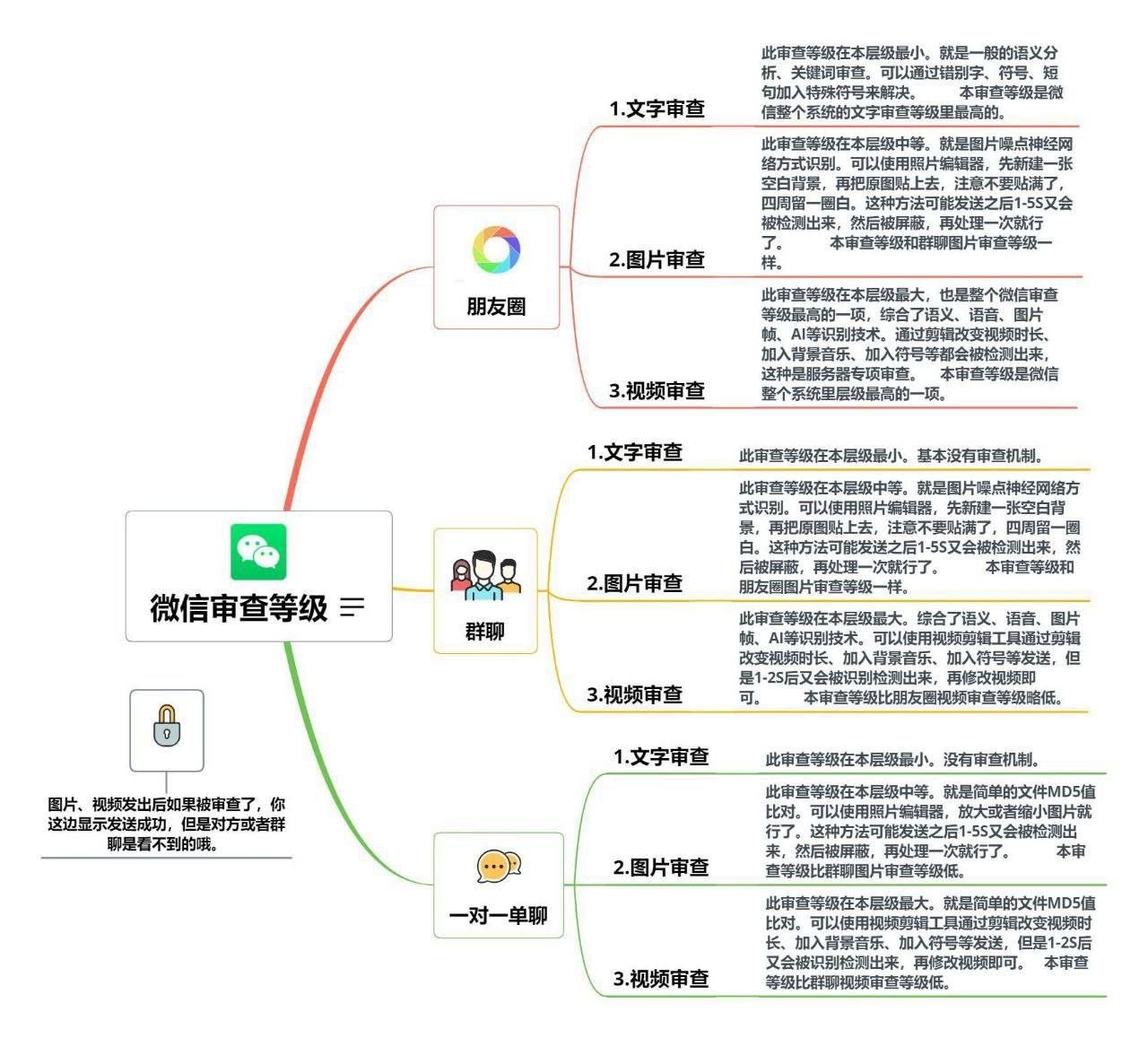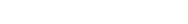鲁迅这位先生,对国民性的卑劣认识的是相当的透彻,骂的也很是过瘾。但他并没有深度挖掘出这种卑劣的国民性形成的根源,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案。
1928年后,通过鲁迅的作品,能看到他明显的亲共亲俄,以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能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剂良药。通过中共这一百年的折腾,已然证明这非但不是良药,却是毒药。
这也难怪他看不清,一来他在日本学了半拉子的医学,是个二把刀的医生,能看的清病症,但找不到病源也搞不清正确的治疗方案;二来呢,当时的苏联深藏铁幕的背后,它犯的那些残酷罪行和撒的那些弥天大谎很难让人看得清。更重要的,当时宪政共和的社会制度还没有通过二战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的自由世界新秩序用七十年时间证明其优越性,不少学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或许是可以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尝试,这是当时所面临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因此,鲁迅后来被当成中共利用的思想工具。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这就是鲁迅思想的困境和悲哀。
(Visited 120 times, 1 visits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