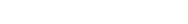过去的已化云烟,随手摘几片云朵玩味一下,既不是凭吊,也不是放不下。 没什么放不下的,也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所有经历的人和事,包括自身都会烟消云散……
一
当年教经济学的是一位本硕博连读的本校土著,三十来岁,礼貌温和里透着一股桀骜,又带点邓丽君式的优雅浪漫。
那些复杂的经济学公式,她总能娓娓道来,随手就能写一黑板过程推算。我从来没觉得枯燥,反而深感理性和逻辑的美感,有时还伴随精神的高峰体验…
后来,她成了我的…
论文导师。
有次在她办公室聊天,我问她“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轻狂?”
当时她杏目圆睁,很理性的看着我,波澜不惊,不紧不慢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我回答,“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然后就看她掩着嘴吃吃的笑。

二
樱子是我在车协遇到的。她读社会学系,身量苗条,体格风骚,说话时笑靥如花,清泠悦耳。每次见到她,我的心跳都会轻微的加速。
一天晚上在南操场做体能训练,她和管院女生一起跑百米,我在旁边为她加油。跑完后,管院女生高兴的找到我,笑容可掬的感谢我为她加油…她也笑着走过来,和我擦肩而过…

三
上学时认识一对朋友,男的读化工,女的读中文。贵州山区来的穷孩子。有时我们会一起去南门外的阿郎家常菜吃个饭。
男的毕业后去了一家基金公司做分析员,女的在家写小说。两年后在朝阳北路买了100多平的房子,又过了两年,换了个西单更大的。
你永远猜不透中国股票市场背后利益输送的管道有多长。

四
咨询公司有个经常跟着我谈客户的清华小美妹,自称系花,有一天在我家楼下吃完晚饭,赶上下雨,她跟我到家里去拿伞。
外边雨越下越大,她不想走了,还跟她妈打电话,说在某某同学家留宿。那天晚上雨下的真是大。我完全没动她,快午夜的时候找的士把她给送回家。
是不是很不怜香惜玉?

五
初次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一家蛮大的单位,当时留着长发,一副满不在乎放浪形骸的样子,也不知道哪个部门的姑娘,找了个媒人想和我见个面。
见面后聊的挺开心的,后又托那个媒人跟我说她挺满意的,想要跟我一块看个电影儿。我拒绝了。此后单位有人就开始偷偷议论我是同性恋。
有什么关系呢?清者自清。
六
住我对面有一对法裔夫妻,60岁上下,男的乐队指挥,女的是管理顾问,每次见面都亲切的招呼,有时还主动过马路聊一会儿。
隔壁土耳其裔家办婚礼,他们举把太阳伞在自家车道上看半天。前年男的要去青岛参加音乐会,还找我学了几天中文。
今年见了我兴奋地说,他考取了舍布鲁克大学的音乐硕士,要去读书了。

七
系里搞迎新晚会,同舍一哥们上报的独唱曲目——吻别被选中了。
此后一段日子,宿舍里天天都是吻别,这哥们勤奋的简直了不得。这首歌从低音到高音各种调调的,可以说我都听过了。
就在要上演的头三天,这首歌突然被撤下了。哥们郁闷的一直到寒假都闷闷不乐。
此后吻别了300多个,这也是一种报复么?

八
九零年代的北京,暮春天气,风沙刚过。路旁的槐树都绿了。和一同学乘公交,车上人不是很多,但也没坐。站着。
不知从哪站上来两美少女,其中一个从后边紧紧贴着我。一路晃晃荡荡。我也没躲。美女从东单下了车。同学酸酸的问我,挺舒服的吧。我讪讪的笑笑,啥也没说。
那天我一身牛仔,穿的太厚了…